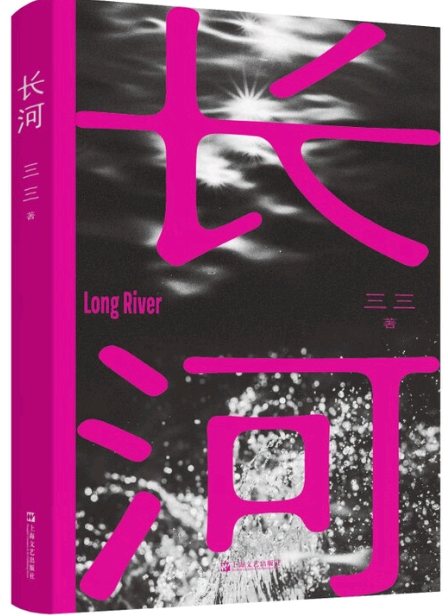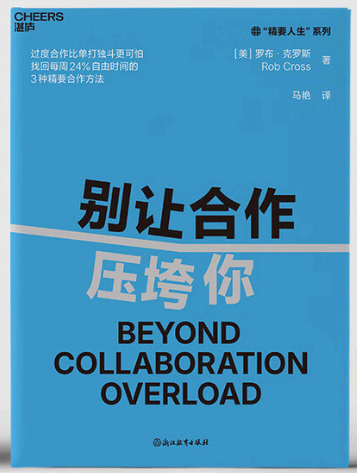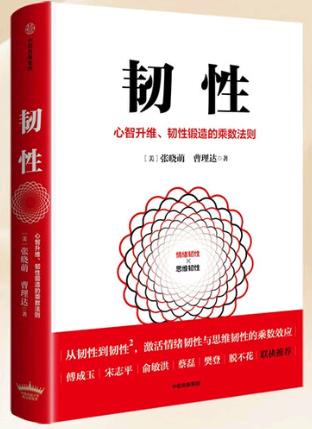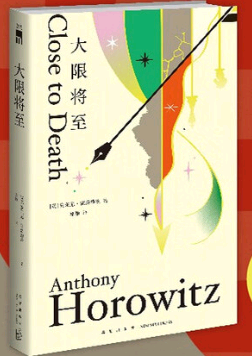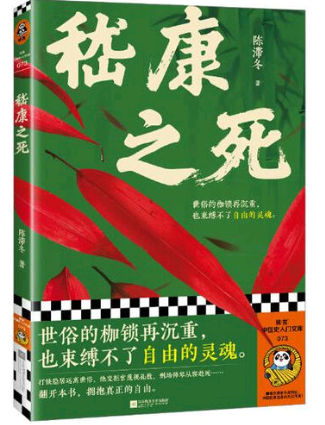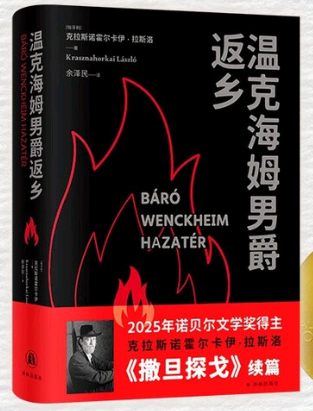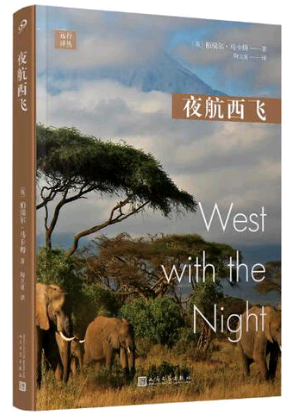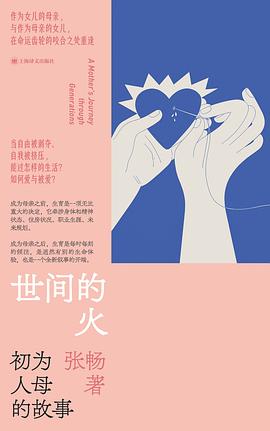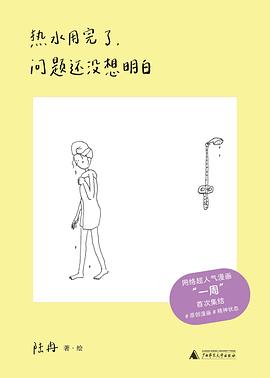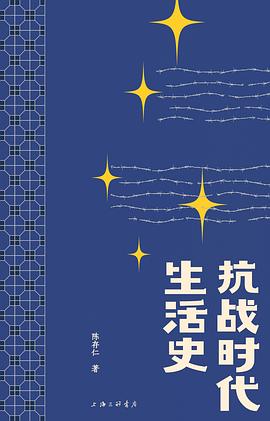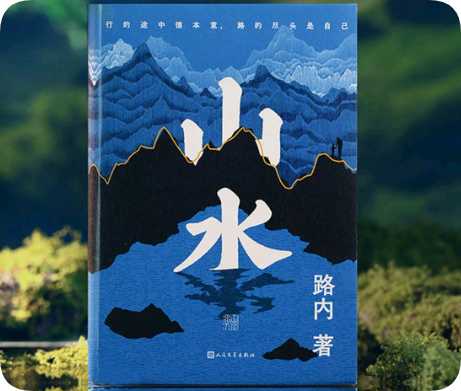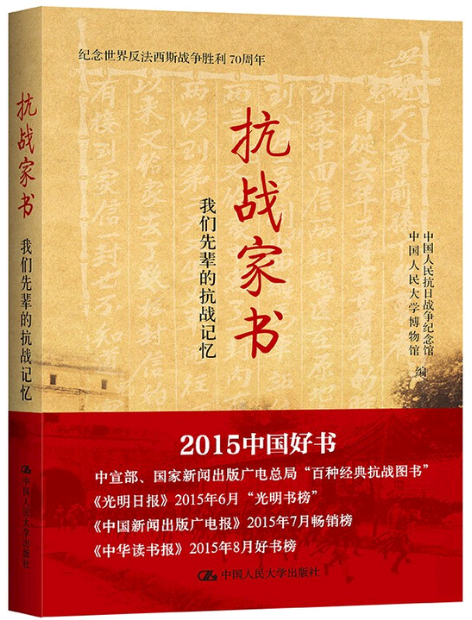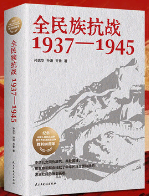作者:雷莉,刘思柯 著
本书作者兼具多年律师从业经验与企业管理工作经历,深谙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全书各节围绕公司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内容覆盖公司设立、经营、解散与清算的全流程,聚焦于公司治理中的热点与难点法律议题,以及合规制度建设的实务要点。所述问题均来源于公司治理实践中的高频法律需求。
本书以问题为导向,结合现行法律法规与企业实际情况,援引典型司法案例,逐步展开法律分析,并最终提供专业律师提示。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通过本书获取公司治理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操作路径;企业法务及从事公司相关业务的律师亦可将其作为实务工作的重要参考。